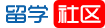记者节征文 新闻5年:在时代里行走
一、 碎梦之获
日子,壮阔的和平淡的,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划过。海浪卷起沙石,还有贝壳、海底珊瑚,一层一层往沙滩上淘洗,岁月的风沙沉淀出一地斑斓,拣拾者扫视时需要心境,以及由头。2004年11月8日,第五个记者节即将到来时,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刚好也走满了5个年头。这5年对于风起云涌的中国报业及其由它所纪录时代风云,已定格成历史;而对于一个参与并见证着新闻里程的我来说,个人的经历多少也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两个“5年”碰巧汇合,我也动了去史海翻沉的念头。
人生再宏大的理想,萌动之初,也就是颗粒大的梦想。追梦者恰如粼粼波涛中涌动的海浪,他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能否抵达岸线。但因为有梦,许多看似无序、无规则的偶然,却终也包孕着某种运气,将你往梦之初的地方送,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就是这样。
梦涌动得厉害是在高中时,高考填报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或许力尚不逮的北大中文系外,其余,我发痴发狂般一口气填下的全是新闻系,其中就有复旦大学和湘潭大学。但现实简直是玩笑般将我的新闻梦撕了个粉碎。想起自己从深圳打工半年,尝遍人间辛酸挣来学费所圆的新闻梦,不过是上帝之手随手泼墨而挥溅出的一个绝望句点,我第一次看到了人生的灰,极度的灰。这还不算,也就是那年,在去查高考分数时遭遇的一次毁灭性的车祸,车撞断了合抱围粗的电线杆后仰翻,前面直逼20多米高的悬崖,同车中有人当场被车内栏杆将背刀开一般切开了至少有30厘米长的、深入骨髓的伤口。我在生死一瞬间的惊魂中竟然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出来一摸,也就是右脚踝处有点痛,外伤而已。看着车内血淋淋的哀号震天的人们,我仍不敢相信,刚才一瞬间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同样是那年,考试后3天去县一中填报志愿,填报完毕后同学聊一阵子就分了,我正准备回家,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痛,便在一家商店的椅子上躺下来休息一下,我想用瞌睡来驱赶痛苦,没想到2个小时的迷迷糊糊状态一旦过去,腹部痛得人竟然已经直不起来了!我强拖着身体,往县人民医院走,1公里的路走了半个小时终于抵达,这时我就得感谢高考期间一位经常生病的哥们,也就是经常陪他来这个医院,对于以前连医院门往哪边开都要找上半天的我,才对挂号一类的程序能够自己完成。医生的诊断也让我大为吃惊:肠痉挛。说,如果再迟到半个小时,恐怕就没救了。生理盐水和葡萄输入我的身体后,2个小时,我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地往家里赶了。我仍清晰地记得,离开医院时我刚好还能剩有路费,而以前我口袋里是从来没带这么多钱的,那些刚好是高考花剩的。
我无法说清楚那一切的遭遇到底是命运的“垂青恩顾”还是刻意捉弄,虽然迷信的母亲给我请算命先生在早前给我算了,说我已进了“七煞运”,一切需细致谨慎,否则有生命之虞等等,这些预言也并不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但经历了生死变幻和比死亡更难受的生存之后,我总算明白并接受了一点:看透人生的虚幻后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身生活,这样就没有什么能够将你击倒。我从小是个骨子里很悲观的人,许多的弄不懂的世界大问题和生活小问题常常让我沮丧。记得上初中那阵,鲁迅那句“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折磨了我许久。我始终无法明白,既然人生都是一场悲剧,那么人为什么不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得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受苦?那时我也弄不明白,扮演小人物的演员,为什么到了生活中又成了众人追捧的“大人物”了呢?为什么生活中的小人物就得不到大家的尊重呢?这些问题我都把它写成日记,一天父亲无意中翻看后大吃一惊,说通篇写的怎么都这么悲观,看不到一点希望?他压根就想不起这些希奇古怪的问题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可这些问题却实实在在把我折腾得够呛,虽然大都虚幻而不切实际。但也就是经历了那次大学新闻理想梦破灭和期间遭遇的两次生死变故后,我仿佛脱胎换骨,性情由悲情弥漫转而豁朗达观,经历催我早熟。我与同龄人有了许多不同的思想。
二、如是采访
或许是因为悲观至极而归于乐观的心境此时已在我心中破土成长,在我看来,大学里一切就都成了顺境。我选的是中文,前景不出意外,应该是去当教师。高中基础学打扎实,加之自己还算得上是一个用功的人,文学方面也有点天赋,在那所普通的大学里,我逐渐显山露水。第一个学年里,我把自己一年里写的小说结集在校内印刷厂印了本小说选,也就在这时,我又开始升腾自己的新闻梦。
第一次外出采访是我和班上的同学阿永一起计划的。今天说来有点好笑,当时和阿永聊天,他无意间说起自己的家乡湘乡有一所高考补习学校很有名气,可惜外面人很少知道。我脑子一闪,这不是可以做个新闻吗?一说出来,阿永也来神了。于是我们顺着话题聊,越聊越兴奋,最后竟决定第二天就马上去采访!而之前我也只是在校园内采访过一些小新闻,对于真正单独挎上相机带上采访本和社会正儿八经打交道,心里是全然没底的,而朋友要我去,当然是我唱主角,全部希望都押宝在我身上了!
阿永用201卡先联系学校,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竟在含糊一阵后答应了!好家伙!那天一早,我拿着校园版采访本,阿永借来一架破相机,背上书包,出发了。
从湘潭火车站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一下车我们直奔这所以高考补习生升学率高而闻名的学校。其时我们直扑校长办,他还在上课,等到中午时来了,没想到他的态度异常平淡,只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自己从学校里跑来的吗?”得到肯定答案后,他说,我们这里没什么好采访的,你们去找其他学校去吧。说完就走了。
一来就吃了个闭门羹,我心里吃惊不小,说好的事怎么又变卦了呢?
我们不打算就这样空手而返。可校长眼下摆明不接受采访。我们商议,大概是觉得我们学生采访了也没地方发表吧?于是又扯整衣冠,露出一副自己觉得很成熟的面孔再次来敲校长的门。
一进门我说,校长您误会了,我们是湘潭某某报纸的特约通讯员(这是真的),文章如果写得他们满意,那里的报纸和杂志都会答应帮我们发表的。校长看了我们一会,不置可否。一阵沉默后,他终于将眼睛平和地投了过来:“你们发表文章不要赞助费吧?”
我们轻松了!当然不要。接下来校长同意了,于是我们忙乎开了,阿永拍照,我提问采访,要命的是,此时我的脑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空,除了“为什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成功经验”、“对社会有什么呼吁”之外,我感觉老虎吞天无从下口。急不出问题来,我忙乱中想到了资料,果然,校长叫办公室人员搬来一大摞材料,有经验总结,有成绩,有分析。我搞不懂的,照单全收,空空的书包一下子鼓囊起来。忙乎了4个多小时,我们总算感觉心里有底了,于是握手道别,这时校长也客气了,送我们出门时说,文章发表了千万记得给他留一份,寄来或者他亲自来拿,都行。我俩头点得像鸡啄米。
回去时间肚子一直在叫,搭进了100多块伙食费来采访,我们做到十分节俭,中饭靠校长的几杯茶镇过去了。但回去的路上仍清晰记得我们都是兴奋的,吹着口哨,湘潭的夜色从来就都没美过那夜。
报道是我第二天对着材料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一直坐在主教楼里鼓捣出来的,中饭仍是一瓶开水,倒不是没饭钱,而是来回去食堂的时间。那天从教室出来后我感觉自己大脑已有点恍惚,但近万字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已将一切代价化作清风淡云。文章出来后我拿去教我写作学的陈老师那里去请教,他仔细帮我修改了,说,写得还可以,只是文学味太浓了,通讯也要讲究叙述的。只是,你们准备拿到哪里去发表?
我们脱口而出是某某日报,陈老师笑了,这类文章要是在我们学校报纸要发的话,也没有这样的版面啊。我们听后暗暗出汗,心就凉了半截。
文章最后被压缩成5000字,我们拿到校内花了20块钱请人打印了出来。阿永联系的某某日报看了后说要学校盖公章后才能发,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学校。带着打印稿他再去找某某日报,报社说,这类文章都是需要版面费的,这篇文章版面费要2万元,给我们打折,至少也还要9000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发表文章还要自己出钱的,采访之前我们预想文章发表后几百元的稿费梦就这样被粉碎。这篇通讯至今仍躺在我的书架里。结果失败,但过程中的锻炼依然是真实的,失败的地方那样醒目,以致让我们回头时依然能够看清。实话说来,当时之所以还能够写得像样,还因为是通讯,与文学紧邻,若是要做一篇纯粹的消息稿来写,那怕800字,我想若不求助老师,凭我俩也要把手写得“韦编三绝”了!
三、激情之初
既然开始,就得继续。大三时在陈老师的引荐下,我来到了一家晚报正式实习。带我的老师也曾是他的学生,一个比我才大几岁的很有才气的小伙子。
我在湘潭市租来一间门面住了进去,月租也不算贵,50元。门面老板是一个下岗阿姨,就在隔壁开盒饭店,我吃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安心学写新闻吧。第一天老师说是带我去采访,结果进了一家超市拍照,老师在匆忙中拍摄了一通后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就要走了。
随后却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其时正在谈恋爱,我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他去看望四川的女朋友,一去就是10多天。第二天刚好有个采访,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一次春节前打假行动,检查时,我用自己那架花200元在二手市场买的“凤凰”相机拍了许多现场查封的照片,完毕后一起吃饭,我熬不过劝,喝了3杯白酒,回报社时感觉耳根在发热,由于一些检查的数据还没出来,我不便写,便干着急,其他老师告诉我,你先把消息写好,等电话问来数据再填进去就可以了,要不等到截稿了就什么都来不及。我的第一篇新闻稿就这样写出来了,第二天的报纸放在头版,图片就都不要了,发了500字, 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的消息稿上署有自己名字的文章。
其后,艰难可想而知了,没有部门的通知,我就只好干等新闻来,等得烦闷了,就挎上相机背上书包(里面有报社配发的采访本、实习牌和一瓶水)自己出去找,在我眼里,什么都是新闻,又什么都不是新闻。那种带着任务出去闲逛的滋味比烈日下的焦渴更让人难受。于是我又想到回报社办公室。大概是我每天早上提前跑到办公室将地板和过道拖得干干净净的习惯感动了其他的编辑和记者吧,终于,报社邻坐的编辑杨老师给我出题目了。她要我去湘潭的几大彩电市场转一圈,去了解今年春节前市民购买彩电的新动向。去之前她反复交代了采访要点,我都记在采访本上。
这类非事件性新闻对我这个非新闻系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入门的快捷键吧,第一篇调查非常成功,杨老师特意给我配发了一个图片,文章也发了一千多字。其后,依照模式,我采访了水果市场、服装市场、旅游市场……采访水果市场时一个插曲是,市场老板大概觉得我给他做了宣传,当场要送我一箱贡梨,我从来就未曾碰到过这类事情,之前也从未有人告诉过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吓得一跳,合上采访本招呼没打就走,没想到他派人用车将梨捎上硬是追到了我一把塞了就走,那个春节每天睡觉前几乎都在吃梨,这就是我第一次收受人家的“物质”了。事实上每次吃起来感觉味道总有点怪怪的。
那年春节我仅在家待上两天又回报社。新年里湘潭的街道多么的冷清,深夜12点后,陪伴我的是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白天,我仿佛成了真正的记者,做盒饭的下岗阿姨笑我说,你回来得越晚明天报纸上的文章就越大。那时确实有一种激情,那激情不知道来自何处,仿佛枪子儿一样等待迸发。而关键的还是,我感觉做新闻已经上路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第二天拿着印有自己文章的芳香的报纸去读更让人满足的事了。那时我的文学理论老师也常在晚上时骑车来看望我,一起分享白天故事和报纸新闻的快乐。那真是一段我今天仍万分留恋的青春时光。
等待激情的迸发的报道终于来了,一天我走在蔬菜市场,发现菜农纷纷埋怨菜价低,有菜农甚至将大白菜倒在池塘里也不愿来卖。一个菜农给我讲了个笑话:种菜为了什么?育肥!育肥为了什么?种菜!我当时听了也不甚了了,跑回去与杨老师说了。杨老师一听,说,你打电话到市蔬菜办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
电话过去,蔬菜办的人话就多了,我了解到的大致就是一个“菜贱伤农”的问题。于是一篇文章交了,杨老师看后,仔细批道,没有写到点子上,再深入了解,挖掘出隐藏的东西来。
那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烦闷的是我那几天都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每晚写到凌晨2点,6000多字的报道,写着写着自己又感觉乱了,等满意了第二天交上去,杨老师红笔改后,说,还可以挖掘更多的隐藏的问题来。于是又采访去了。
修改了4遍后,杨老师再没退稿了。也就是第二天,报纸一个整版的《沉甸甸的菜篮子》配大幅照片发表了!市领导打电话到报社来了,报社一位领导署名“张三”配发的专题评论《沉甸甸的话题》将这篇调查再推深入。第一次看着自己的新闻报道将整版报纸都占得满满的,我的心中除了波澜,还有泪水,那不是一个狂喜就能够形容得了的。
到了此时,曾被新闻系无情地拒之门外的我,或许能够心地宽慰的是,在报社4个实习生中,春节前一次对民工的调查采访中,总编安排我牵头,带了湘大的一个学生,在湘潭火车站实地调查。文章第二天被头版头条推了出来,虽然最后都没署实习生的名字,但多少让我感到:梦想的彼岸在一天天地靠进。
四、梦与等待
梦想中的新闻是一种必然,但从大学里跑出来干新闻于我也实在是一种偶然。记得那时学校里文艺活动比较多,我那时凭借一点实力??更多的是学生相互之间的传播,弄了一点名气,于是台词的脚本大都落到了我的头上。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一个叫林琅的经常在学校里主持节目的女孩子找我借东西,说到了毕业后去向,她在长沙一家报纸应聘,便极力怂恿我去。被她说得心动了,我跑到长沙。那是一家和湖南某电视合作创办的一家报纸,其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没想到我一去竟然真的被他们看中了。于是在10余个朋友的竭力劝说下,我签约了。
我当然不知道当时全国报刊市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只记得来长沙那天天气很好,冬天的阳光开得和夏天一样灿烂。4个兄弟帮我背着行李,将我卖给了孤独的长沙。那时的我心底仍涌动着实习期一般的激情。
一年后拓宽眼界后我才知晓,那实在是一家小报,他当时并未来笼络多少人才就匆促上马,在全国市场报此消彼长风起云涌的时代潮中,它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给它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在创办人被窝尚未捂热的时候,各种隐性的显性的矛盾集中了。我写的创刊词还来不及发表,于是宣告停办。眨眼的工夫,我失业了?!
失业于人总是夹杂痛苦和失落的。一个7岁的小孩会因为失去一个装笔的廉价纸盒而哭上一整天,一个17岁的少年在笑7岁小孩的同时,同样又会因失去一个叔叔从美国带回的书包而难过上一天。当年曾被视为悲苦的失去,哀痛是因为当时视为真谛的理由,而人生好在目光总是落在身体的前面。
这是一个机遇丛生的时代。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告诉我某某在创办一家大学生的报纸,取名就叫《大学周刊》。作为创办参与人,我进去了。之后酸甜苦辣,也非此文所能穷尽。略。四个月后,我通过应聘,进了一家大报,做起了经济新闻。这段时间给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学会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人生,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天地。
我做的第一个经济新闻是某蜚声海外的彩电厂家为了促销而与某旅游城联合促销的事。当时我实在不甚了了,蒙头做了,老总说不行,便不断启发,也正是从这里,我感觉到了商家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火花四溅的谋略。我当时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优势,或许是因为我的潜力,让领导产生了送我去上海培训4个月的决定,对一个非经济专业的人,这是入行最快捷的途径。但我最终选择了放弃,我终于发现人的个性与专业之间也会存在隔膜,而这些隔膜与专业知识、技能无关。我理想的新闻首先应该是人文的新闻。选择放弃恰好也符合了我的心态:等待。
五、激情之旅
今天看来,我真正的新闻生涯应当从我做纯粹的社会新闻的那一天算起。而我的最彻底成长,应该也是从这时算起。
从诸多的应试者中一路走出,大型综合类日报全新的都市报业理念在我没有任何条框的大脑中开始构筑新闻的模型。
在经过让同行揣测万端的全封闭式培训后,我预先被安排在编辑组。但我给自己的选择是:社会新闻,更确切地说,都市新闻。每天背着相机,揣着采访本出入长沙古城,从每一个最细小的地方去感受这座城市,而自己也在逐渐地被消融进去。每一天的发现,总是新的。每天的采访虽然将时间占据了一大部分,但晚上就寝前,我还是雷打不动看上一阵书,几年下来,还真看了不少在今天看来仍十分重要的书。
无数多的发生在长沙城的故事,构筑了这座城市的另面真实。当更多的事实,无论是轻快的还是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总会去探究它背后深藏的本质。
一次我参加的报社编前会上,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新闻:一个在湘江里打渔的老船夫,发现对面乘快艇的水上公安在执法的途中遇上一个风浪,翻船了,于是年近七旬的老船夫挺身而出,将两名公安人员从水中救出。派出所对老船夫当场给予嘉奖。这确实是一条很好的社会新闻。
但报社随即有了质疑的声音:公安的快艇被一个风浪就吹翻了,这样的快艇合格吗?不合格又是从哪里买来的?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快艇?水上公安尚需要老船夫去营救,这样的公安人员合格吗?他们是通过怎样的考试进入公安队伍的?难道这一切事实的发生,都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当真正的“新闻眼”被抖出来后,虽然让人触目惊心,但新闻的层面无疑已被前所未有地拓宽了。这也是促使我从预备从事件性社会新闻报道向深度报道转型的一个转机。
后来在周报从事的深度报道采访中,新闻环境又让我有了许多感触。一次是一起被诬陷为强奸少女的案件,考虑到诬陷人能够让诬陷对他人构成已然伤害的事实,我的采访便做得十分仔细,都是直接的一手文字材料和录音证据。报道出来后,当地引起轰动,可破案的进展却是缓慢极了,这似成惯例,让人愤懑,又让人悲哀。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就是案件当时人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一篇报道出来,当事人无一例外就是感激涕零。这感激很容易让他们首先想到物质表示,而这又无疑与新闻界最忌讳的“红包”搭界了。我曾不止一次地与采访对象说过,采访与被采访只是工作关系,而人情与工作关系绝对不能混同。可你一旦真正做到采访一完立马就走,他们会茫然不知所措,各种揣测也会不期然而至。最坏的揣测无非就是,你嫌他的招待不周,不再替他主持公道,已经决绝而去了。而等报道一出来,他惊喜中绝对会跑到报社来看望你,而看又绝对不至于空手,于是再次带上了他大包小包的“物质表示”!在这样一个整体的人情化的大环境中,所谓纯粹的记者,真的又成了一种理想。如果等到一天,市民能够坦然接受记者的应有的帮助,社会真的又前进一大步了。
社会存在许多的显规则,但更多的是潜规则。即便在新闻圈里,潜规则依然存在,而且也可能剧烈。当“新闻民工”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便成了切身的感受者。这个时代定然会过去,走过去,又成了历史,触手及处,我能够感觉到历史的温度。我们这批人所接受的,也正是“记者”社会声望和地位江河日下的现实。不管曾有过虚假新闻,不管甚至有过的新闻内讧,等等。我仍愿坚信,媒体是一个时代的良心。而新闻记者,正是这良心的寻找者(而非拥有者),一个记者,要保持自己内心的独立和个性,就必然需要承受独立的能力:新闻才能和经济独立。新闻才能让他具备“自由之思想”,经济独立让他具备“独立之精神”。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发现自己又似乎陷入了理想主义的泥淖。
经历了人生,从少不更事都逐渐老成,新闻生涯让我碰到过无数多的人,见识了无数多种的生活,产生了无数多次灵光一闪的火花。这样带着故事跳动的火花,我把它捕捉下来,于是有了两本书——《被透视的我们》和《逼近灵魂》。
至少,到今天为止,我心中已把这两部书当作了自己理想职业生涯的驿站。我不知道新闻到底有多高,也不知道别人已经爬了多高,但我比较清醒地知道,从理想到今天,我就这么高而已。
六、三十而惑
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老了——这句话出口似乎太突兀,又太快了点。
我不是说眼看着比我更年轻的又都冒了出来,我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就跑不动了,我只是说:我做新闻已经老了——更确切地说——我做新闻的心态已经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丧失了激情更让人悲哀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个人再大的定力,在一种潮流的裹胁下,总是显得不由自主般的轻飘。更何况时代的新闻行业本就是一个催生浮躁的职业。我曾经想拥有什么,我曾经得到什么。人生有梦,可梦成梦又归何处?就在前脚才刚刚迈进30岁时,我以看透自己后再生发的一种乐观告诉自己: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祈望能够从工作中得到快乐。
这也是一种奢侈么?
70年代这群人,最大也就34岁,最小也才25岁,如我者,正是折中。从年龄上无论怎么界定都是青年一代的一群人,让我在心里暗暗祈祷:惟愿我有此心态为一特例而已呀!我有时候甚至在想,花5年时间将所有的新闻都尝试遍了是否节奏太快了点?这似乎是理由,但我心底感觉又不是。
若说生命的长度,时间是它唯一的标尺,若说生命的厚度,信息量可作标尺。人生的许多种追求,失去或者得到,再也没有比充盈的内心更让人满足的了。到今天,我仍做着网络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可我不经意间已毫不客气地将自己从新闻队伍中剔除了出来。新闻是充满激情的事业,可我如今眼中只有任务,我只知道要完成,却没有创造的快感。没有创造感的新闻人,在我心中,他充其量只能够说在工作。
是的,我在工作,5年可以改变一个人。于是我特别怀旧,一个哲人说过,怀旧是心态衰老的标志。而且,怀旧需要由时间堆垒出来的距离。连怀旧都显得心虚的时候,我只好说:怀想未来。
那次,我给湖南一所大学做讲座,面对底下晃动的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我无来由地羡慕起来,他们,多好!我知道又如何?至少,他们可以津津有味地听一个大哥在讲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勾画他们心中的梦。可我的梦?它曾经有过,可今天,它不是破灭,而是,不存在了。它去哪里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在纸上仍如痴如醉地继续勾画我的梦,可我的心会时时提醒我:它是假的——我不想阿Q式地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让阿D喊痛。
难道今天就已没有让我醉心的事情了么?我想有的:钱。这是一个常常把我折磨得异常郁闷的东西,为什么要避讳?尽管做新闻时一想到钱人就有点恹恹的抬不起劲了,可没有钱我连身体的寄存地都找不到了!我真羡慕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他一看见钱,眼睛里就立即会放出金子般的光芒。那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人生体验。我想有那样的时刻,我也会放出异常的光芒的。只是,另一个不安又悄然袭上我的心头:在瞬时的体验过后,我会因长久的空虚而至死么?——我又不是葛朗台。
有同行与我说起,35岁那年,他想离开新闻行业,可是不行了。他已不年轻了;除了新闻,其他的他已经不会干了;毕竟,自己还爱着这个职业。你是否同我一样,已听出了他的些许无奈?——同行又不是我。
莫非,大自然有意地设置了许多人生的神秘,只可解读,不可读破?读破将作何解?曰:让他丧失激情。难道,新闻是一个看透人生神秘之所,自然又是一个沦丧激情之地了?
理由最后自己还是不知道了——其实无非才5年啊。